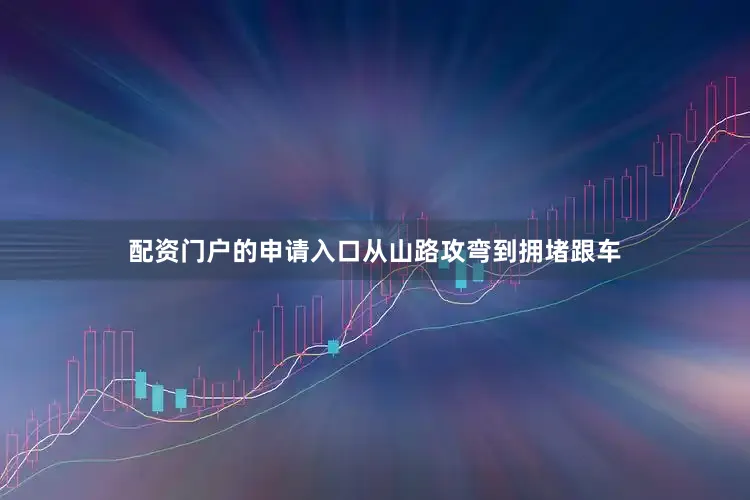63岁陈冲出新书,写的不是“优雅老去”,是“把生活大咬一口”的狠劲。
翻完她的散文集《猫鱼》,突然懂了为啥这书能刷屏——她不跟你讲“岁月静好”,偏要把人生拆成碎片,再用文字拼成带刺的花。
写作这事儿,陈冲说得特直白。就像有人用相机存照片,她想用文字拽住那些快消失的时光。书里写外婆的蜘蛛网、母亲的失眠、自己疫情时冒的白头发,全是“一切都已经失去了,却还想再拽它回来”的执念。
她写母亲去世那章,我盯着手机屏幕半天没动。她说“人生最大的失去,好在只有一个妈妈,再经历一次怎么受得了”。这种疼不是煽情,是把心挖出来晒在太阳底下——原来所有怀旧,都是和“失去”的较劲。
30岁生日那天,她看着满屋子像葬礼的鲜花,突然觉得“青春过去了”。可后来又乐了:“原来还能继续挥霍,一直挥霍到死。”这哪是告别青春?分明是把年龄标签撕了,重新给人生贴便利贴。
展开剩余66%很多人怕老怕到睡不着,她倒好。疫情时穿了半年睡衣,某天照镜子发现“好像突然老了5岁”,后来翻到科学研究说人44岁和60岁会突然感知衰老,她笑出了声:“原来我的发现不是错觉。”把个人体验和科学对照着乐,这劲儿特有意思。
她不怕皱纹不怕白头发,怕的是亲人受病痛折磨。聊到死亡,反而像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——“从生出来那天开始,我们就在走向死亡,这有什么好焦虑的?”老照片里的自己“还真挺漂亮”,当年倒没觉得,现在看倒像在看别人的故事:“这个女人怎么就变成我了呢?”
有人说她人生像坐过山车。19岁拿百花奖站在“中心”,后来去美国演尸体、端盘子,掉进“边缘”。可她偏不这么想:“我这辈子就没觉得自己在中心,也没想过要回中心。”演戏对她来说,不过是“一不小心当了演员,后来爱上了创造角色的过程”。
在美国的日子,文化冲击像冷水浇头。她想念上海的梧桐树、弄堂里的吵嚷,说“乡愁是一片永远失去的天堂”。可她没困在怀旧里,反而觉得留学“拓展了地平线,让我看到整个世界”。现在的她,能用中文写上海弄堂,也能用英文聊剧本,三种语言在身体里长成了新的根系。
金宇澄说《猫鱼》填补了上海知识分子叙事的空白,她倒自嘲“文化水平低”。没正经上过学,真正的阅读是从留学开始的。但她身上有股子知识分子的反骨——“最走红的东西,我永远是怀疑的”。
写《猫鱼》对她来说像“劳作”,没什么神秘状态。往电脑前一坐就开始写,按时交稿。63岁的人了,把人生过成一本摊开的书:不遮皱纹,不掩不安,用“大咬一口生活”的狠劲,把每个平凡日子都嚼出滋味。
最后突然懂了她书里那句话:“越老越像自己,因为没力气遮掩了。”衰老哪是枯萎?是终于能剥开所有壳,露出里面那个一直鲜活的灵魂——就像陈冲,63岁还能蹲在文字里,把生活咬得滋滋响。
声明:本文中信息来源于网络,不保证完全正确无误,仅供参考。
发布于:江苏省富明证券-短线配资炒股网-券商配资开户-股票杠杆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